东南西北
条评论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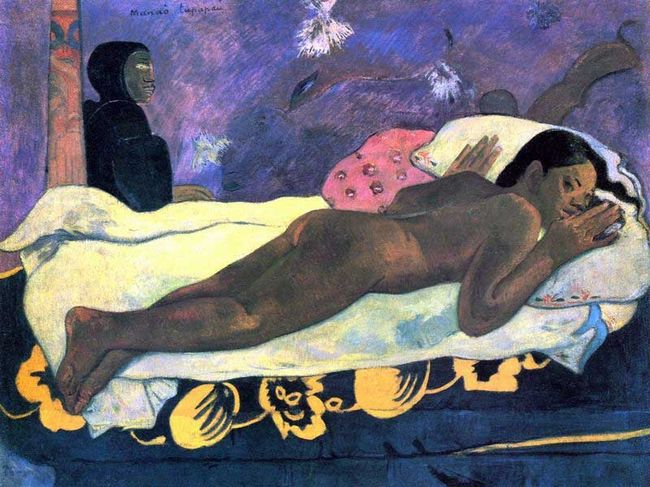
一、东去
这座城市的门窗紧闭,在煮饭的在煮饭,在做爱的在做爱,在猜疑的在猜疑,在逗猫的在逗猫,一切井然有序,没有突如其来的干扰和意外如雷的波动。一到二十区还是那个样子,看似像个少女迷人得要命,但莫名其妙的味道仿佛是个腐朽的老人,带着花枝招展的虚妄,让你嗤之以鼻。夜晚的塞纳河迷迷糊糊,被下了迷魂药,埃菲尔铁塔硬硬得戳起要非礼她,梵高捧着一堆话,说没办法,没办法。
九区的一个老板娘,还是在甜品店里不干活,毕竟她也是老板,可以为所欲为。在桌椅之间游荡和穿梭,世界各地男人的目光是她日常尘世间的滋养,一眼两眼三四眼,一天要吃好几顿。我朋友欣赏她的美貌,觉得不能让任何一个美貌女子在巴黎的冬天饿死,所以常去,维持她们的营生。我被拉着去了一次,当时点了个玫瑰千层,在我吃到五百一十九层时,老板娘出现了,俊俏,成熟,像个销了皮的白雪梨,香气霸占着周围的氧气。我没有逃避我的义务,给了一个大眼神,目光如不灭的油灯火,从下到上,她一天的滋养也就够了,便到门口去点了一根烟,她已经学会了法国姑娘所有该有的姿态,连臀部也往上进化。但我没有把她拥抱在怀里的冲动,毕竟她跟她嘴里吹出的烟一样,很快就游走。我朋友没有领会这一点,每周六去,变成了一个胖子。
二、西行
对岸,初开的梨花第一次落入三月春水,很凉,将水流的路线缓慢刻画下来。再远些,山腰的遗雪逐渐收拢,暗色逐渐扩大,雪水一滴两滴渗入泥土里消失不见,在午间汇成细流后,才及时托住第二片落下的梨花以及梨花的影子。摊开新路,朝着更远处流去。屋外,还是冷涩,你将还未化的雪放入炉火上的陶壶里,煮掉一天似长似短的日子,跟梨花一样,落了又开,开了又落。对于此刻来说,昨日和明天,透过陶壶口的蒸汽,在你的眼里,虚乎而且缥缈,存在又不真实。
我到达屋外时,听见你冲茶的声音,你招呼我坐下后,一言不语,仿佛把什么都说了,仿佛又什么都没说。这样下去是一场爱的活动,伤感主义与性的集合。茶水之上加上爱,就能制造模糊意识里的酒了。
三、南下
凤凰山白云寺向南半里,是乌雀庭,亭中四块石圆凳,围着四方的棋盘石,石上步着《当湖十局》尾局,棋止二百手,黑子为方,白子为圆,暂不能看出黑白胜负。石刻的棋子,缺残得像个老人,手欠的旅游行人,休息时会无聊敲砸棋盘,在没事中找点事,棋盘因此更加破烂和残缺,分不清方圆。黑白子之间,模糊不清,但懂棋之人,今仍能看到棋盘上,棋子的仙气向上弥漫,仿佛当年范、施两位棋坛高手犹在,时间静止,犹如初晨湖面的雾气。
乌雀庭往北半里,是白云寺。盛夏午后,沙弥小强问白云寺寺主庋一禅师:“叫我如何不想她,想她木兰青双绣缎裳下的身体,和对我吐字时的语气?”沙弥小强问出时,寺后树上的知了仿佛都断了翅膀,突然而至的安静,使得空气更加炎热。
“想源于不想,不想而生想,她就是无她,无她而生她。想她就是想无她,想无她亦是不想她。”
“住丈,这无半点逻辑可言,我会疯掉傻掉糊涂掉。”
“逻辑出现是为了阐述逻辑,文字的被造是为了延续轮回。”
“住丈,叫我如何不想她,想的尽头是什么?”
“没有尽头。黑子白子,无第二也无第一,无第一,亦无第二,第一手,也决定了最后一手。”
“住丈,叫我如何不想她?”
“你不要再问了,回去生火,我要吃南瓜。”
四、北上
我于一棵松柏树上初醒,困意未尽,鸟窝越来越抵抗不了冬天,冷风从松柏树外拐着弯得杀进来,再从巢壁疏细的空隙中杀进来,再从我身羽毛的空隙中杀进来,断断续续得来,没完没了。我想多长点毛,不怕臃肿不堪,就怕挡住看山看水看你的眼睛。
清晨树下路面上雾气还在下坠和纷飞,石路还很潮湿,像宣纸上未干透的散开的淡墨。松柏针簇之间,能看见的月亮,不知道在哪个方向什么时辰早已沉落下去了。我昨夜准备画它下来,唯是无法抓住它的静,于是弃笔。没有心思的专注,是脱离队伍的鱼。懵懂木讷的双眼,因为想你,而更加懵懂更加木讷,所以人们老是傻鸟傻鸟得说出去,喜欢没有理由地加一个傻字,嬉嘲云云。
选择建窝的柏树,在你窗不远,二三十米,我飞过去,扑打翅膀十四下。这条路上,是我们两构建的故事,我喜欢这故事的末尾带着不确定性,就如开头见你带着偶然的运气。在所谓的爱情中,智商和理性总是在请假在远方,全世界的人若都在爱情之湖里,这个世界早就崩塌爆发经济危机,得幸还有很多人撅着屁股使劲干活,于是忙里偷闲得以继续念想。禽类转动脖子,总是一瞬间三十度,一瞬间六十度,一瞬间九十度,是以为你的脚步声,才会进化成如此。水的唯一缺憾是重力,我的唯一缺憾是生有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