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七三月辑雨水不会跳舞
条评论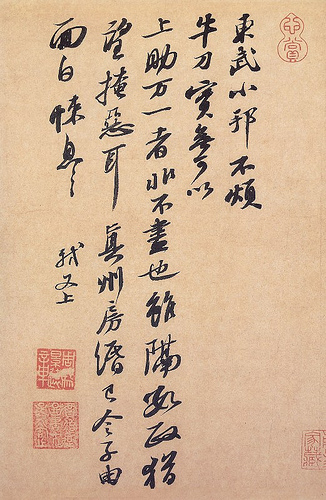
语言和文字,没有统一没有极限,到达极限只是作家们安慰自己的幻想。鹰击长空,鱼渡厚水,文学突破语言的局限,又在扩张语言的渗透之地,预知埋藏的不确定性猜想。写字的人经历磨练,增加敏感度,又要抵抗时间时常带来的厚茧。少时作品不能改,虽通灵不达,聒噪穿插,但自有喜感。
—
诗人活在仙境
厌视一切规则
包括写诗的规则
—
可不可以不吃午饭
这样就不会有下午
可不可以不亲吻你
这样就不会有结束
—
诗是受难的体验
如同突围后的鱼
禁锢在自由的地面
—
如果长生不老
我不会再有意识
也不会再想念你
—
三月的日子在深碗中睡着
泡过的茶叶
浮不起一个白日梦
—
广播侵犯了空气
恶俗的音乐
软弱的柳条摇晃着诉求安静
—
匆急的爱情在朦胧雨中飘摇
湿漉漉的石板
一个个行走的吻印
—
六十年代的退休老兵跟我说,跟爱人写了十七年的信,十七年里就见了一次面一小时,一小时里他送爱人从家走到火车站,买了火车票,送走爱人,看着庞大的火车,装着快要溢出的悲伤。
—
六十年代的老兵跟我说,不同时代人面对不同时代人的问题,他们拿着筷子和小盒子去捡拾战友的遗体,战斗机爆炸后,战友也粉碎,一根毛在树枝上,一块碎皮在石块缝中。
—
六十年代的退休老兵跟我说,一百多岁的父亲去世后,才有空来巴黎看儿子媳妇还有孙子,孙子一句中文也不会说。我说,您有自己的生活,他们其实跟您都没关系。